◎妮可
拿了皮鞭不一定能當一個好女王。感謝有你陪我一起成長。
因為SM、讓我們相遇,共度歡樂的時光。
未來很長,但願這些回憶永存心中。
◎epicure
7/23 日晚上,乱田舞在乱舞館的表演過後,乱舞館 master 引介我們認識德國來的訪客。我自我介紹後並聊了幾句話後不太進入狀況地問道「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?」對方一愣,身旁的 Akaneko 遲來地提醒「欸,他應該是很有名的人唷… 」
Drachenmann (漢字名「龍神」),是德國 SM 雜誌 Schlagzeilen 出版者之一,同時也在德國做 SM 表演。這趟來原本要替雜誌訪問明智伝鬼的,不幸明智伝鬼在約定當天過世而失之交臂。
稍早一週龍神也在安排了一場表演,以下是他提供的照片。目前他主持繩縛網站Bondage Project(德、英、日文)。看來繩縛在西方也發展得相當蓬勃呢!
◎妮可
我特地挑選這天去乱舞館,終於和乱田舞有了比較近距離的接觸。總覺得看到乱田舞,就像看到偶像般的喜悅。笑容洋溢的自己,有點不太真實。從幻想到實際,如同夢境一般。還記得第一次看到的成人雜誌,有乱田舞。對著這陌生的名字沒有太多感觸,只知道是繩師,大篇幅的照片吸引我的目光。接下來的幾年,看了許多SM的片子,對乱田舞的影片特別感到興趣。因此對於乱田舞,有著許多的刻板印象。
今天是七月二十三日(星期六)。 大約下午四點日本發生地震,JR 線跟部分地下鐵都停止運轉。因為地震而交通中斷的情況真是無法想像。過了三個小時後電車才開始運轉。原本跟 epicure & akaneko 約了要一起吃飯,也只好做罷。跟 vivi 在路上找間店吃點東西,接著就到乱舞館。
八點多,依舊是我和vivi最早到。通常乱舞館是越夜越精采,我想今天也不例外。接著 是epicure & akaneko進來,epicure 一進來就喊累,說整個車站都是人,等候了許久。我想,經過百番波折,得來的果實應該會更甜蜜吧?(笑)
稍微休息了一下,epicure 和 akaneko開始練習橫吊。在epicure 快吊好的時候門鈴響了,Master(註) 去開門,我心想該不會是乱田舞來了吧?果真是乱田舞!他提著行李箱,從門口進來的時候,看見我們還稍微點點頭做打招呼狀。epicure 看到乱田舞,則嚇了一跳攤倒在地上。
或許是看過許多乱田舞的影片和照片,對於他的長相一點都不陌生。刻板印象中的繩師總是嚴肅而有氣勢。不過乱田舞給我的感覺卻十分親切,非常有禮貌。或許這才是現實生活的乱田舞吧!人總是有著許多的面具,隔著螢幕,我看見的並不是真實的呈現,往往只從修飾過的戲劇效果中去幻想。讓我不禁深思,真實的 SM 是怎樣的呢?我們是否因影片中看到的 SM 而抱著太多的幻想?
乱田舞的魅力果然無法檔…今天似乎也來了許多蠻有名的人!大約九點多,狩野千秋來了,我們跟她揮手說「好久不見」,不過這個好久不見說得有點心虛,雙方都笑了出來。因為十九個小時前才見過。昨天我們去渋谷的 Primo,狩野千秋的店。夜夜笙歌的日本生活…
乱田舞的表演,是那麼有魄力。精采滿點!舞台旁邊,放了三根蠟燭,形成一個三角型。熄燈!音樂一開始,Model穿著浴衣跪臥在地板上。配合著音樂,乱田舞用手抓起她的頭髮、親吻她、撫摸她,用麻繩緊縛她、滴蠟、鞭打。每一個動作都深深吸引著我!
龍神是一位德國人,在她旁邊是兩個白人女M。在乱田舞的表演之後,他也開始表演繩縛。不知道是否是國度風情的差別,總覺得他綁得特別緊,多了幾分力道的呈現。
至於接下來發生什麼事…
秘密!不告訴你們!
註:日本的店長我們通稱Master。
以下的照片是乱田舞與 Akaneko. Akaneko 另寫了三篇日記(epicure 則簡單地附上中文說明),詳見 Oriental Bittersweet.
◎ Ralph(原作于 2004/6/18)
據說,事件發生的那年,曾有過一棵櫻花樹,花色如火般深紅。
大概是那年氣候變動大,比較奇怪吧?詳細的情形,由於年代久遠,已經無法深究,只在故老們偶然的閒話中,得到些許想像的蛛絲馬跡。在滿山盛開的粉色中,只有山頂一點鮮豔的紅,自遠處眺望,大風吹過時花葉飄散,頗似女子鮮嫩的私處之上,沾上一滴燭淚的奇異景象。抑或是如淚般的血滴?沒人說得準。口耳相傳的越久,記憶也如被風吹落的凋謝葉片,逐漸枯乾碎裂。
那是個多風的春夜,一對男女上了山,坐在樹下喝酒。隨從早早就被遣退了,只剩下他們兩人。那天的山裡很靜,幾乎一點聲音都沒有,只有柴火偶然因燃燒而發出的輕微爆裂聲,以及不斷吹送著,托著粉色紅色綠色的花葉的,嘆息一般的微風。
酒差不多飲盡了,男子順手把手上的杯子一放,掉在席旁的地上,殘酒慢慢的滲入土壤。「真美。」他是仰著頭看著櫻花的,但女子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在稱讚自己,因而有點嬌羞的低下頭來。女子身上單只有一片薄紗,除了長長的兩袖,再沒有任何裁剪,只是隨意交疊在身上,風一吹撩起下擺,修長的大腿就被火光映得紅豔豔,如同因酒酡紅的雙頰一般。女子偶爾移動身體,如同順服的寵物在主人面前撒嬌一般,變換著不同的姿勢,展露自己的身形。有時動作大了些,薄紗經那麼一拉,「衣襟」就這麼展開,露出大腿根部隱隱約約的肉色恥丘,或者是堅挺的乳尖,女子也只是無聲的嬌笑著,然後漫不經心的隨意拉扯一下,就當著已經整過衣了。
「可為我,再舞一曲?」他轉頭,望著自己心愛的人。女子望著男人微微笑著的神情,也回以柔媚而順從的微笑。男子一襲黑衣,若不是火光映照,在深深的黑夜之中,幾乎等同於消失了一般,可櫻花花瓣零零散散的灑落在身上,猛一看,像是幾點妖紅的星辰,在深邃的黑暗中閃爍著。
女子起了身,風一吹,又是無數花葉飄散空中,零零落落的灑在女子的長髮上,的身上。男子支起身體端坐著,開始不斷重複著,曼聲吟起一段非歌非詩的奇異文字:
「
今日櫻下舞隨風
恰似相識當時無心雲漢遊
只是髮結紐
無奈燭火燒斷
此後天南地北不相逢
休 休 休
不如飲鳩忘憂
攜手渡泉劃破愁
任紅蓮燒灼當是白頭
」
女子隨著吟詠的節奏,開始舞動身體。先是慢慢的揮舞衣袖,如同撲螢一般,劃弄著墨色一般沈重的空氣,然後抬頭望著樹梢擺動的枝葉,自己也跟著甩動肢體,此時女子的肢體,又像是肉色的柳絮,夾雜在火光之中搖曳著、飄動著、飛舞著….薄紗不知何時已經掉在地上,只有裸身的女子,在漫天紅青之間展示自己的舞姿,隨著吟聲畫出的地圖,把生命散在四處,然後如枯葉慢慢的萎去。
男子的聲音越來越快,越來越悲哀,女子也隨著越舞越快,越舞越狂亂。突然,男子一陣抽搐,聲音如同被硬生生的自空間中抽離一般,嘎然靜止。同時,女子的腳步也一滯,蹣跚走了幾步,軟倒在男子面前。兩個人彼此相望,不斷的喘息著,像是兩隻瀕死的野獸。
花瓣在兩人之間不斷的飛散著,有一葉停在女子顫動不停的胸口,隨著心跳而鼓動。男子直勾勾的盯著那片紅花,突然一把將女子拉過,瘋狂的舔吻那花瓣所在的位置。女子發出了細碎的呻吟,撫摸著男人的臉。男人的口唇從吸吮成了啃咬,動作越大,女子的呻吟聲也逐漸加大,仔細注意,可以聽到其中隱含著的痛苦,但是手卻越發溫柔的撫摸著男人,彷彿是要用手記住男人的臉一般,非常仔細而緩慢。
男子抽下了衣帶,將女子的手綁住,另一端則纏在櫻樹的枝上。女子保持半坐躺著的姿勢,但手被吊在樹上,等於是把身體整個展開在男人面前。女子的身體由於運動與酒力,已經染上了淡淡的櫻色,就著火光一看,彷彿光的波紋灑在身上,畫出深深淺淺的不同痕跡。男人順著那痕跡來回的撫摸著,有時輕柔的像呼吸,有時則近似要撕碎女子一般的粗暴,但女子除了因快感而呻吟,或者因痛苦而扭動身體之外,沒有任何抵抗,她的眼睛仍然溫柔的望著他,他帶著血絲的眼,像是母親看著受苦的孩子。
男子拿起旁邊燭台上燒了整夜的短燭,呆呆的望著。燭淚慢慢的流淌,流到他手上。刺痛讓他回過了神,換了手斜持著蠟燭,然後看著燭淚滴在女子的身上。灼熱使得女子不斷的扭動,但是身體受縛,總逃不過燭淚的侵攻,於是只能掉著淚,看著身體各處不斷堆積的紅色丘陵,體會隨之而來的火燙,那比男人進入還要強大千百倍的烙印。
蠟燭換了一根,又一根。女子已經露出了恍惚的表情,嘴角流淌著唾液。身體上燭淚跟花瓣堆積著,幾乎到了掩埋住女體的地步。男子將眼前愛人的腿張開,仔細看著她的私處。粉紅色的折皺,不斷的張縮著,像是唱著歌,引誘水手衝向礁岩自毀的人魚,拉扯著男子往墮落的深處一步步陷落。不知道是出自慾望,或者是出自愛憎,男子突然湊過去,狠狠的咬了一口。嬌嫩的黏膜經這一傷,流出幾滴血紅,男子露出了詭異的笑,慢慢的舔去。此時女子連掙扎呼痛的力氣都沒有,只是肢體不斷微微的顫抖著,但,表情是詭異的,也是愉快的。
蠟燭都用盡了,只剩下席位側的篝火,遮遮掩掩的照著男與女。衣帶自櫻花枝上被取下,握在男子的手上。女子如同屈服著,輕柔緩慢的舔著男子怒張的陽具。先是細細的用舌尖勾勒著男人龜頭稜角的外型,然後是嘴唇含著尖端,虔敬而貪婪的吸吮,繼而是盡根含入,忍著喉頭略微的不適來回吞吐著,偶爾又吐出火熱的肉棒,用嘴唇磨蹭,用舌頭包覆,上下摩擦。這回輪到男子顫抖著,露出失神般快樂的表情,不斷嘆息。
接著,男人扶起女子,讓女子倚著櫻樹,翹起臀部。她的身體顫抖著,因為剛剛的火熱,也因為吸吮著男子陽具引出的慾望。男子愛憐的撫摸著她的背,再次喃喃的贊頌著女子的美。酒意已退,女子的雪白肌膚與身上黏著的紅色痕跡,形成了強烈的對比,彷彿生與死的交界變得模糊,疊上慘白,疊上火紅,然後上面再用幾片花葉點綴著自然。男子猛然一送,陰莖竟根沒入女子的蜜壺,採搾著慾望的花蜜,隨著猛烈的抽送四處飛濺。男子的低吼,女子高亢的淫聲,配上肉體的撞擊聲,彷彿火花四濺,在林間隨風四處迸發,惹得篝火彷彿也回應著,紅熱的飛灰在風中如螢不斷飛舞,飄動迴旋著,環繞交纏的肢體。
良久,柴薪也將燒盡,夜色逐漸將四周的景物吞進,只有著黯淡的火燼,隨著心跳一般的節奏吞吐著光芒。兩頭野獸在激烈的嬉戲之後,平靜而頹然的對坐著。女子再度將男人的陽具放入口中,但這次的動作幾乎感受不到慾望,而只是發自內心的愛意與溫柔。男子撫摸著女子四散的長髮,眼中的血絲不知何時已經退去,取代的是如同潮水一般的深湛。然後男子勃起了,完成任務的女子,抬起頭對著想望著的人露出了有點複雜的微笑,男子點了點頭,彎下腰也開始舔起愛侶的私處。受了那誘引,女子的身體又火熱了起來,深處的慾望也開始在下體凝聚,氾濫。
兩人又恢復對望,同時慢慢的,但堅定的對著彼此微笑。男子自身後置放的小鐵箱中拿出了一小瓶酒與兩個杯子,為兩人斟滿。已經不再需要確定彼此的意志了,因為在放情的交合中,在眼神的對望中,他們已經說夠了。於是,兩人碰杯,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,接著女子起身,坐在男人盤坐的腿上,讓陰莖進入私處。兩個人的慾望,在此時經由彼此的連結,不斷的來回傳遞,膨脹,漲的彼此又熱又渴(或許是毒酒的藥效發了?),兩個人先是吻著,輕輕的,然後越來越重,接著開始啃咬彼此:舌頭、嘴唇、臉頰、耳朵、頸子….並不是溫柔嬉戲的輕咬,而是每一下都留下痕跡,滲出血的激烈啃咬,彷彿要將對方一點不留的吃下去一樣,而手也從緊緊擁抱,到了撕扯刨抓對方血肉的激烈程度,可下體的抽送與收縮,卻依然緩慢與溫柔,彷彿是他們正享受著彼此最後的精華,帶著不捨與珍惜。
夜櫻如火般的落花,不斷的灑在兩人身上。地面上事先循著特別的軌道倒上了油,在黑夜裡好似蜿蜒的河流,上面飄著花瓣與兩人接合時的白濁噴發。此時,兩人累積忍耐的慾望也到了極點,女子帶著嘶啞與抖音的呼喊聲突然靜止,隨之而來的是從最深處爆炸開來的,帶著各種光影與聲音的,無邊無際的高潮。強烈的收縮也如同最終的呼喚,呼喚著男人的精華。回應著這祈求跟誘引混合的間歇收縮,男人也將自己,完全的給了出去,填滿女人最後的慾望。
保持著相連的姿勢,男子手一揮,篝火倒了,頓時地上的河流變成了火炎奔流的赤色通道。兩人被火包圍著,卻沒有被火給吞噬,只偶然有幾點火星,逃竄般駐在她髮上,他身上。櫻樹開始自根部被火沾染,散出如同薰香的味道,慢慢的將兩人的血肉榨乾,再換用香氣來填滿,花的香氣,樹的香氣,火的香氣。
風不斷的吹著,花葉被捲上半空,又被火場產生的上升氣流這麼一托,好似依依不捨的,在一片豔麗的赤色中盤旋回顧。火勢變大了,燒著花瓣,好像花瓣長了吞吐不定的翅膀,終於往遠處飄去。
然後,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在山頂的大火結束之後,附近的居民在山頂那棵紅櫻樹的殘骸旁,找到一對乾屍,面目跟身體都被撕裂的模糊,無法辨認身份,但仍然維持著死前交合的姿態,分也分不開。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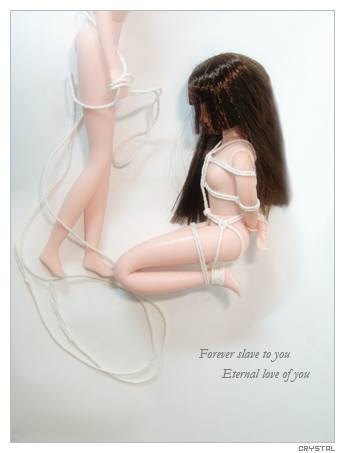

以下是我的手肘自縛法之一。請切記,手肘自縛可能是最危險的一種自縛方式,若有不慎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。不要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練習。
本文的手肘自縛使用了上回簡易自縛一文中的技巧。如果不了解簡易自縛,也難以了解手肘自縛。基本上,我先把身上的飾繩綁好,然後把繩子繞到手肘上,利用固定物體把手肘拉緊。最後繫緊手肘,並把手綁在下半身。
明智伝鬼於 7/17 日上午 10:36 分辭世,享年六十四歲。
◎ Unsatura
應該是小時武俠小說時期的殘餘浪漫,我總認為,鞭,是眾多工具中最性感的。它性感的地方在於其千變萬化的使用方法;snapping, punching, whirling, falling, wrapping…。每種打法給予不同部位不同的感覺。打起來時,主人的動感隨打法及部位的轉換而變更,配合奴隸的顫動,活像舞蹈。
(有主人不認同以上的一些打法,認為危險。輕輕的打就不會危險了。記得,只打有厚大肌肉的地方,不打骨頭或關節,不打小背,手腳末端,臉。這就該安全。)
鞭子好像是有性格的,你要和它建立良好的關係,它才會為你服務。用它是須要耐心練習的,不像藤板或棍,這些硬物,要打得準實在是太容昜。
以前有幾條寬帶子的皮九尾。寬寬的軟皮帶重重疊疊地落在皮膚上實是很美麗。殺傷並不高,衝擊力都被寬帶的面積分散了。但使用手法有限,因為寬帶吃風。也因為只該讓平面落在奴隸身體上,施打動作幅度及方向都有限。打起來有點不俐落或甚至笨拙的感覺。
要找到適合自己的鞭子不容易。我的短鞭已不再是皮做的。皮鞭,要有適合的硬度,重量,並不昜。價錢高又難清潔及保養。膠質材料,重量硬度的選擇都比皮多,清理容易。唯一不好的當然是外表和味道。所以,我通常都不讓奴隸看見我用什麼鞭他。
短鞭,九尾,可以用另類材質代替。但我想,長鞭,到目前是只能用皮做的,因為要編織,而且是非常複雜的織法。我覺得沒有任何材質可以被皮更好了。
但長鞭非常難買得到,也因較貴,不願意從綱上購買,怕買到手感不稱的。在香港的Fetishfashion見過一條非賣品,聽說是老闆娘朋友做給她,讓她調教時使用的。閒時用來陣列;怎麼說也不肯替我訂做一條。看得心非常癢。也非常心痛,因她沒有好好的打理她的工具,隨便捲起來放著。不,鞭子是要垂直掛的。
不過用長鞭的機會不多,因為空間昂貴。沒有幾個遊戲場地是夠用長鞭的。偶然找到一個也沒有用,因為長鞭須經常練習。多希望一天能找回失去多年的武功,再次有機會揮灑盡致。
◎ Ralph(原作于 2004/8/16)
首先,要感謝皮繩網站的朋友們不嫌棄,在徵求我的同意之後,把一些過去的舊文章帶過去,打算分期刊登。趁這個機會,自己也回顧了一下過去的一些想法,然後,胡言亂語的老毛病就這麼被引發,趁著興致來了,稍稍為過去的文章加點現在的想法,就當是眉批吧?
在這圈子裡,雖說不是什麼經驗老到的人,但是這段時間,跟不少S性與M性的朋友聊天,算是增長很多見識了吧?感覺上,每個人對BDSM都有些自己的想法,或模糊不明,或清晰堅定,但是至少是個表彰自己信念的概念。只是,每個人的概念或多或少,都有些不同,這與其他方面的信念一樣,不同的信念,在接觸時總會或多或少,發生摩擦,也許產生火花,也許產生爆炸,端看差異與雙方信念的強度大小。
不過,在我的感覺,BDSM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特化的,比較複雜的人際關係:互動方式因為位階上的差異而有不同,性向的差異也會導致認知的不統一,而在溝通上發生的問題,除了可能引發心理層面的破壞,也可能造成生理上無法磨滅的傷害。當然啦,複雜歸複雜,要簡化來看,還是人跟人的互動關係,所以,從這個基本認知開始推演,就可以很簡單的得到一個有點陳腔濫調的結論:「你的真理,不等於我的真理。」或者,改成複數形式好了:「你們的真理,不等同於我們的真理。」
在這樣的關係中,奴從的真理,是對於主人的信任,或者可以說是崇拜,主人的真理,則是自己對BDSM的認知與信念,以及衍生出來的,對奴從的期許與要求。基於這樣的前提,主從雙方的互動,是以「配合」這個概念為前提,真要說的話,比較接近舞伴(之前學舞學了一陣子,總是會想到這些),彼此在音樂之中,互相配合舞動。跳探戈的時候,放探戈的音樂,但是舞池中,每對的動作並不會一樣,而是在一個大原則之下,取得自己舞動手足的空間。
我更喜歡的另一個比喻,是印章。印章有兩種刻法,一是陰刻,就是將字畫線條的部分除去,讓印章印下時的線條保留空白;陽刻則相反,是只留下線條部分,印章印下,只有線條的部分有沾墨,而留在紙上。把主從分別當作陰刻跟陽刻,在理論上,雙方應該可以緊密相合。不過,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,總是沒有那麼順利的,大部分的狀況,都是經過不斷的磨合、溝通與適應,才能確定彼此的主從關係,互相信賴與認定。當然,我們可以說,人都是具有一定彈性的,不像是印章,大多用石頭或木材刻就,彈性較不理想,可是呢,「信念」這麼一回事,就是越堅定越好(笑),當對於一種生活態度有了自己的認知,想去作大幅度的修改,大概也只能等待巨大的刺激發生,引發改變。所以,在這方面我可能抱持著比較保守的態度,會覺得人們可以試圖改變,去配合關係中的另一個角色,但是改變的幅度大概不可能太大,否則就是信念被曲折摧毀的結果。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,同樣的,每個SM傾向的朋友,也有自己對這種特別的生活方式的選擇權利。並不是別人來告訴你,什麼是BDSM,而是自己去吸收知識,去反芻與消化,而得到自己的概念體系與信心來源。不過,不可諱言的是,這個圈子因為特異性的問題,會讓些掙扎中的新朋友們無所適從,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或喜好「正確」與否,這樣的煩惱,時有多聞。其實很無奈的是,這條路並不好走,在與社會主流價值方向不同的狀況下,走在這條路上需要的,是更多的引導與鼓勵,還有提供廣泛的客觀資訊,供人研究、思考與用來評估、檢視自己。我認為,這是先進來這圈圈幾步的朋友們,所該扮演的角色,所該提供的資訊。
新生的幼苗,是最有可塑性的,正如同尚未燒製的釉土,刻印上怎樣的紋路,出窯之後就帶有怎樣的紋路。如果,我們是印章,可以在釉土上印下自己所知所聞的事物,那麼,誠摯的期望,我們所印下的,能夠減少主觀的自我,而是盡量客觀的,我們所認知的,這個世界。我,如此默禱著。
◎ Ralph(原作于 2004/4/16)
「過來,」在包廂之中,他要求她。她順從的靠近這個還不是很熟悉的男人,貼著他坐下。
「不,趴在這。」他指著自己面前的小空位。她皺了皺眉,因為他跟桌子的距離很近,要她跪在這中間的小小區域之中,可能不大方便….「趴在桌上,然後屁股朝向我。」他的表情不變,仍然是平靜而不帶火氣的聲音,可她的臉一瞬間脹紅了。「可….可是….」
他沒說話,只是眼睛瞇了起來。她的心裡彷彿有隻蟲在啃食著,癢癢的亂叫人心慌。「這樣的話,他的臉會很靠近….」遲疑著,她這麼想,但面對著他的眼神,那似乎什麼都沒想的細細眼睛,卻很明顯的傳達著他的意志。
她終於開始緩慢的爬動著,然後抬起一隻腳,像母犬一樣,跨過坐姿的他。牛仔褲上,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濕氣,自私處不斷的泛出,那濁熱與濃稠啊!想著他的眼神,她的陰道裡,縐折不斷的收縮、擠壓著,彷彿那視線有質量一般,透過下體的遮掩物,硬挺的插入她的陰道中,填滿了充滿潮濕氣息的淫亂口器,然後,內壁彷彿有了生命,開始貪婪的想要吸吮那如同陽具一般堅硬的,他。
「很好,非常淫亂的姿勢。」「謝….謝謝主人….」「別動。」語詞像鐵釘一樣,固定住她原本因為雞皮疙瘩而顫抖的身體。她想瞭解這個男人,想知道為什麼他之所以是他,想知道為什麼他能驅動自己的另一個部分,想知道為什麼自己會想聽命於他。穩定性?冷徹?溫柔?技巧?其實在顫抖之中,一切都不再重要,現在的她,只能集中注意力在貼著臉頰的冰涼桌面,以及不斷微弱痙攣著的陰道。
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,只聽得到她的呼吸聲,夾雜在外面隱隱傳來的談笑聲中。「好,把褲子解開。」他終於說話了,語調彷彿也有點變化,這從緊貼著他下腹的身體部分,傳來一樣的暗示。她感受到了他的陽具開始堅硬,抵著她的胸腹之間,這彷彿成了種鼓勵,讓她邊舔著自己乾燥的嘴唇,邊試著解開下半身的束縛。這麼跪著,其實很難拉下褲子,而張開的大腿也成了種阻礙,她越來越不耐,下體的搔癢不斷的催促著,但手指卻不聽話….
「好,我來。」他把她的牛仔褲拉到大腿根部,「蜜汁牽黏著呢!從內褲拉的長長的,黏在褲子上了喔。」平淡的語氣,卻讓她羞恥的恨不得把臉埋進桌子裡。「對不起….淫蕩的小奴還沒讓主人調教….就濕成這樣了….」他突然不輕不重的打了她的屁股一下,「啪!」的一聲讓她一瞬間咬緊了上唇。
「是啊,妳也知道自己很淫亂,對吧?那,是不是該處罰?」
「是….是的,小奴很淫蕩,請主人….啊!請主人懲罰….啊~~~」話還沒說完,他的手繼續打了起來,一下又一下。並不是真的很重的力道,痛也痛得細微,但是可以很明確的感覺到他,經過堅硬的下體,經過灼熱的手掌。這疼痛她還可以忍受,只是輕咬著牙,忍耐著不讓外面的人聽到自己的聲音。
「看來越打會越淫亂呢,小穴不斷的流水喔。」他挑開完全沾黏在陰道口上的底褲,注視著她已經因為興奮而大開的陰唇。他的氣息帶著搔癢與溫度,讓她又不由自主的顫抖著,等待著接下來將會發生的事情。「塞住好了。」突然,他把粗大的手指插入了她的陰道,她忍不住叫了一聲,隨即更辛苦的咬緊牙齦,想著外面的人是否聽到了她的聲音。
他的手指相當長,幾乎可以頂到最深處子宮頸的部分。她忍不住,喔,該說是陰道忍不住的,開始吸吮著侵入的異物。那與陰莖不同,柔軟而不斷的靈活改變方向,有時抽送,有時夾捏,有時又輕摳著最敏感的癢處。她的身上不斷的引發顫抖的火花,但是固著的身體只能忍耐著一波一波的衝擊而不敢晃動。「主人要我不要動,可是….好….好舒服….」她幾乎已經開始咬起了桌子,忍耐著快感的侵蝕與折磨。那是虐待嗎?她分不清楚了,只想等著那終末,只想等著高潮。
不斷的收縮,不斷的顫抖,越來越強,越來越頻繁。「要….要….不行了….」她嗚咽著,輕聲的吐出慾望的衝擊。海潮逐漸的淹過胸,淹過頸子,快要讓她被吞食,快要令她沒頂….
在那令人期待的一刻之前,他抽出了手指。巨大的空虛有如突然乾涸的水源地,讓她忍不住劇烈的顫抖、收縮。彷彿空虛突然把自己的內在全部抽走一般,她覺得自己好虛弱,只剩下殼子。
她想哭。
喘息著,她努力轉過頭,試圖想看清那狠心的人的表情。他怎麼可以!怎麼可以把我的快感抽走!可是….可是….他是主人啊….
在這猶豫之中,他的手又突然沒有徵兆的進入了。更強烈,讓她感受到快感之外的疼痛,但也補足了她,用那隻手。她什麼也顧不得了,開始扭動腰部瘋狂的夾弄,發出高亢的呻吟聲,像是母獸貪婪而虔誠的享用著美食,也像是祭壇上獻祭的羔羊被刀刃刺穿時的扭動。